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前同事发了条消息,问最近好不好。对方客套两句后,礼貌又疑惑地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我说真没事,只是突然想起,关心一下。对方表示大受感动。
这个时不时想起某人就发个消息去问候的习惯,是最近四五年养成的。虽然不怎么符合现在所谓的社交礼仪,但我也并不十分在意。对于我来说,就像小时候睡前要盘点自己的画片和玻璃弹子是不是数量齐全、品质完好,我现在需要时常确认一些稍微在意的人的近况。
这些人,若要认真计较,与自己的生活也不怎么相关。只是曾经或深或浅打过交道,有过气味相投的时刻。这已经足够令人长出私心,希望他们少受颠簸,回望时依然如故。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精力被分配得越来越细碎,很多人和事无暇顾及。有时候想起他们时,生活已经进入下一个拐角。
工作之后,我很少回家,最近一些年尤其如此。有时打电话回去,我妈说,你爸回乡下帮忙去了,老家谁谁谁走了。“走了”,就是去世了。而那个谁谁谁,原本可能是我孩童时期很熟识的人,年纪也和我父母差不多,走的理由又相当仓促。
还有些时候,群里某个人突然沉默,过了很久之后再冒泡,说自己或家中遭了什么变故。说者轻描淡写,但我们多少能猜测出背后的痛苦与沉重。
这些事情,常常令我觉得,生活就像一只存放在楼梯间阴凉处的冬瓜。原本以为它外形未变,便会一直水份充足,“卜卜脆”,但有天突然上面发现黑斑,按下去就塌掉一块,接着就有更多坍塌接踵而来。一个人生活的变故,除了极为亲近的人,在他人眼中,也都是悄然发生的。
丢掉一只烂冬瓜尚且觉得惋惜,生活本身,以及生活中那些在意的人,就更加值得时常检视。这便是我偶尔要去打扰他人的全部缘由。
对于生活乃至生命,我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检视本身,其实也藏着我对自己生活状态安全程度的观察。
现在的住处,我住了很多年,从家到地铁站,要横穿一个小区。中间弄堂的拐角处,有个很小的早餐店,应该开了很多年。有一年年后久久不开张,令人心焦。等到终于开张,嚯!老板娘正红大衣,新剪的波波头染成茶色,脸也白里透粉。虽然一身敲锣打鼓,但我由衷为她高兴。
尽管没过两天,她又变回了窝在蒸笼后面黑乎乎的菜色妇人,但至少这家早餐店还活着,已经足够令人心安。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生活半径里就会出现很多“熟人”,有某位喜欢热情攀谈的菜贩,有连寒暄都不曾有过的小店,甚至是一道放了某种很对我胃口的冷门佐料的菜。但无论如何,他们逐渐成了我生活的细节。留意这些细节,便是留意生活本身。如果他们状态稳定,或许就是生活暂且无虞的证明。
不过,变故总是难免的。小区物业被换掉了,他们中一个态度热情但干活潦草的大叔不知所踪;曾经一起拼过团的邻居姑娘搬走了。今年大年初二,我出门时,在小区门口迎面撞上四个黑衣人,正抬着一具遗体送上殡仪馆的车。他们,可能也是别人想要关注近况的那些人。
如今,我的生活稍有调整,但通勤路线仍要穿过那个小区。我早就不爱吃那家店的早餐了,但每次经过,看见小店热气弥漫,摊位上还是那几样,店主照常坐在背后无所事事,觉得也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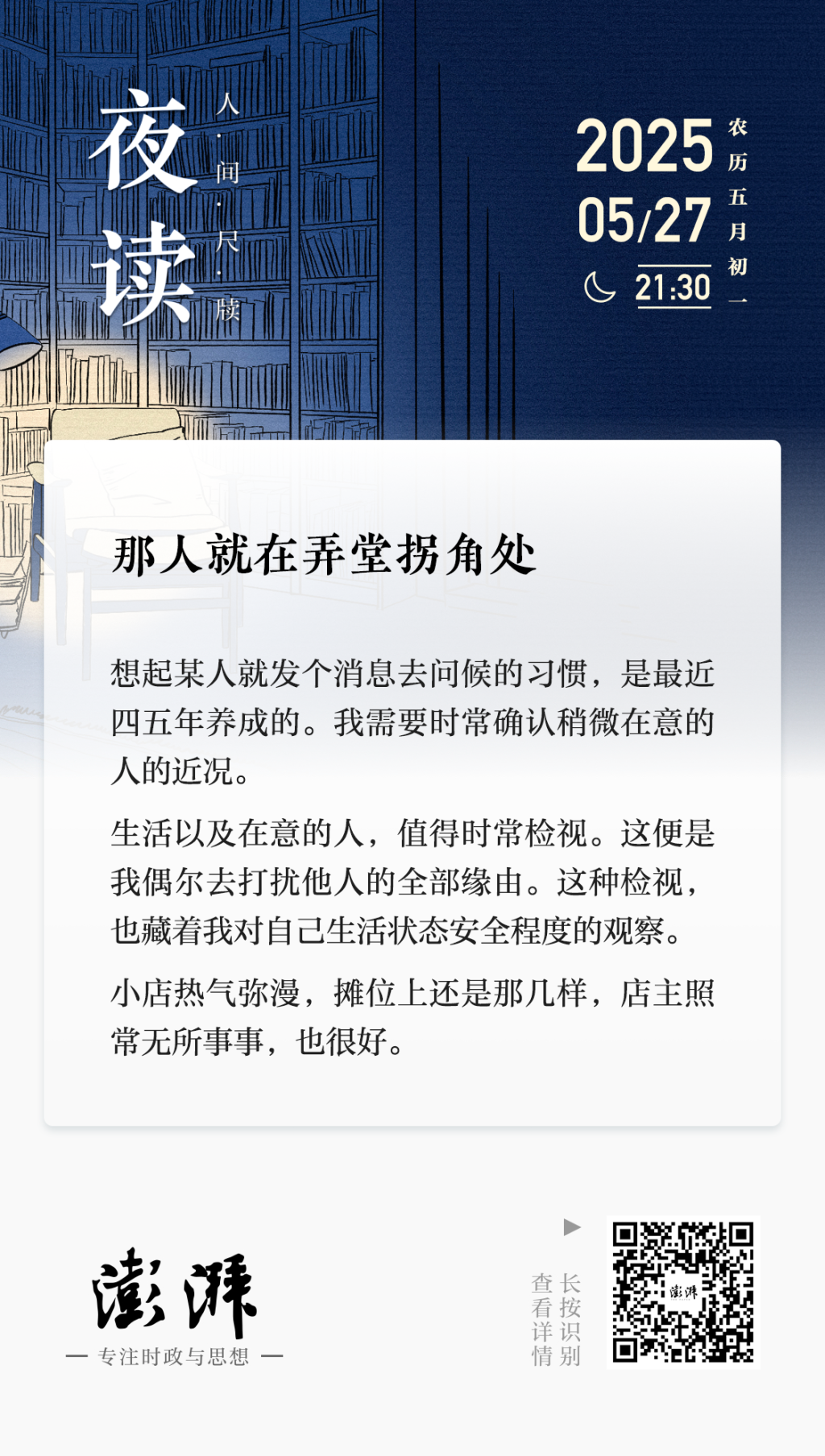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夜读丨那人就在弄堂拐角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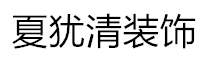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5
京ICP备2025104030号-2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