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澎湃新闻”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晓伟,他的研究领域是辽金元史。

陈晓伟教授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陈晓伟:我主要研究辽金元史,具体围绕三个方向展开:第一,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辽金史相对冷僻,我以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尝试突破辽、金、元的王朝史体系,从“辽金元”的视角探讨相关问题;第二,基于民族语文与传统汉语文献相结合的理念,我注重运用契丹文字深入探讨辽代制度,如四时捺钵制度的历史演变、皇族结构和后族国舅帐的组成、辽代官僚体制的复杂构成等。第三,参加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从事基础性的古籍整理工作。2008年至今承担点校本《辽史》《元史》的修订任务,专著《〈金史〉丛考》提出《金史》整理工作的新思路。
澎湃新闻: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陈晓伟:其实,最初也没有什么学术理想。我从内蒙古师大考研到北师大,是宋史专业,导师是游彪教授,2008年跑到北大历史系蹭课,有机缘旁听刘浦江老师主持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本读书课,后来尝试点校了《杨晳传》和《杨绩传》,但最终效果并不好。好在我写的《〈辽史〉复文再探》通过刘浦江老师的“考验”,有幸到北大读博士,才有机会走上了辽金史研究的道路。我记得是,200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刘浦江老师介绍我认识刘凤翥先生;后来就在刘凤翥先生和康鹏师兄指导下,我开始琢磨契丹文字。十余年来,我和康师兄相互砥砺,探索的道路上不再孤单。解读契丹文字,离不开其他民族语言尤其是蒙古语的辅助,2011-2012年,我获得吴英喆教授等人的帮助,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交流学习,后来又得到乌兰老师指导,能够利用蒙古语知识解决元史问题。2014年6月博士毕业,在刘凤翥先生的大力推荐下,我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工作,正式步入科研轨道。然而很遗憾,我辜负了老先生的很多期许。个人的学术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始终没有达到成熟标准,2018年到复旦后,慢慢认识了以“浪群”为核心的学友们,他们教会我了很多,不仅仅是学术方面。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陈晓伟:学术生涯中遇到的困难与生活艰难相比,不值得一提。对我来说,根据兴趣做自己的研究,并且还在大学里工作,再累,每一天都是幸福的。不过,由于境遇不同,每个学者对“困难”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当下社会,青年学者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现在学术评价趋于“标准化”或数字化,很多科研管理部门把期刊划分了各种等级,迫使学者追求高等级期刊上的发表目标。现在的趋势是,工作越来越难找,博士毕业后,即便找到高校职位,多数人还要经历六年“非升即走”的竞聘考核,这当中,期刊等级、论文篇数、国家级别项目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在一个传统学术领域讲求“传承”,维持“祖宗之法”,形成人们津津乐道的学脉。具体来说,学生要发扬自己老师的观点或祖师爷的学术思想,往往很多论文选题都在这个框架之下,这不免沦为“传宗接代”的代孕工具;而反传统之说,则需要更多勇气和胆识。总之,青年学者治学,谨慎对待“大家”之说,促进学术批评,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应该是被鼓励与提倡的。年龄的增长与学问的进步并不成正比,一个学者要不断地检讨,要多看自己的短板,如果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则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陈晓伟:这个怎么说呢?好的学术氛围无疑有利于学者身心健康,令人向往。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极端环境的学术条件仍会产生的一流作品。辽金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代辽金史学者,以傅乐焕、冯家昇、陈述的学术成绩最为卓越,被学界称作“辽史三大家”,他们很多学术作品都是颠沛流离途中撰写发表的,就此开创了辽金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陈晓伟:除了“上海社科新人”,我还入选过上海市“曙光计划”学者(2022年),非常感谢。从上海整体人文环境到复旦历史系的小环境,是相当友好的,知足常乐。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上海社科新人”的相关课题?
陈晓伟: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契丹文字及相关研究。契丹文创制于辽初太祖阿保机时代,其仿照汉字隶书字形记录契丹语,分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两套文字系统,辽亡后,仍被金代官方沿用,直至明昌二年(1191)废罢。随着契丹人群体的逐渐融合,契丹文字随之湮没无闻。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辽庆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发现契丹文哀册,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达40余件,契丹大字碑刻也有13种,以及传世书籍1件(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尚未公布)。契丹文字是一门死文字,解读难度极大,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目前破译的比例并不高。距离契丹文彻底破译仍非常遥远,不过最近些年来,学界正逐渐意识到契丹文现有释读成果对于辽金史乃至契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目前辽史研究大体以记载颇为简陋《辽史》为主,辅之以为数不多的汉文石刻资料,仅仅依靠这些汉文文献做研究,不关照契丹本民族语言文献,我们的学术视野不够全面,研究深度必然会受到限制。随着释读工作的不断深入,契丹大、小字石刻逐渐成为民族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揭示仅靠汉文史料尚无从知悉的某些重要史实,正在给辽金史带来新的生机。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
陈晓伟:“上海社科新人”不仅给予很高的荣誉,更给获得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费支持。我申请的课题以10-13世纪这个时段为对象,研究这个范围内辽金元政权的统治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由此总结南、北社会特征,统合进程中的政权博弈与版图重构。通过以“差异——互动——整合”作为基本思路,构建长时段、跨王朝史的研究体系,建立“整体史”观,力求突破将同时期的不同政权分割为几个领域的断代史研究模式,将10—13世纪的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揭示跨政权的民族融合与社会流动,以及不同族群在权力结构、文化思想、观念认同上的复杂互动。
澎湃新闻:更进一步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陈晓伟:这是很大的激励,督促我做出更好的成绩,坚持在学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陈晓伟:这个问题比较宏大,需要思考好才能回答。我就是研究历史的,并且还是那么偏僻的辽金元史,作为一个学者,只是期盼着生存环境变得更好,社会生态健康,希望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更加包容开放。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陈晓伟:辽金史研究人少,基础比较薄弱,总体还处于困境之中,尤其是地域性较强,集中在北方,南方专门研究者很少。我自己不仅要多出成绩,还要认真培养这方面学生,通过大家的努力,立足于上海国际化的学术背景和学科优势,慢慢提升辽金史的研究品质和影响力。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的创新挑战?
陈晓伟:要正确认识“智能”和“智慧”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的,其实仍属于非传统意义的体力劳动,它可以提供诸多便利,极大提升工作效率,我们当然要双手拥抱。而一流学术作品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则是“智慧”,教会我们做人。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陈晓伟:突破王朝史体系,拓展“辽金元”研究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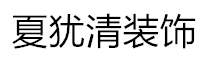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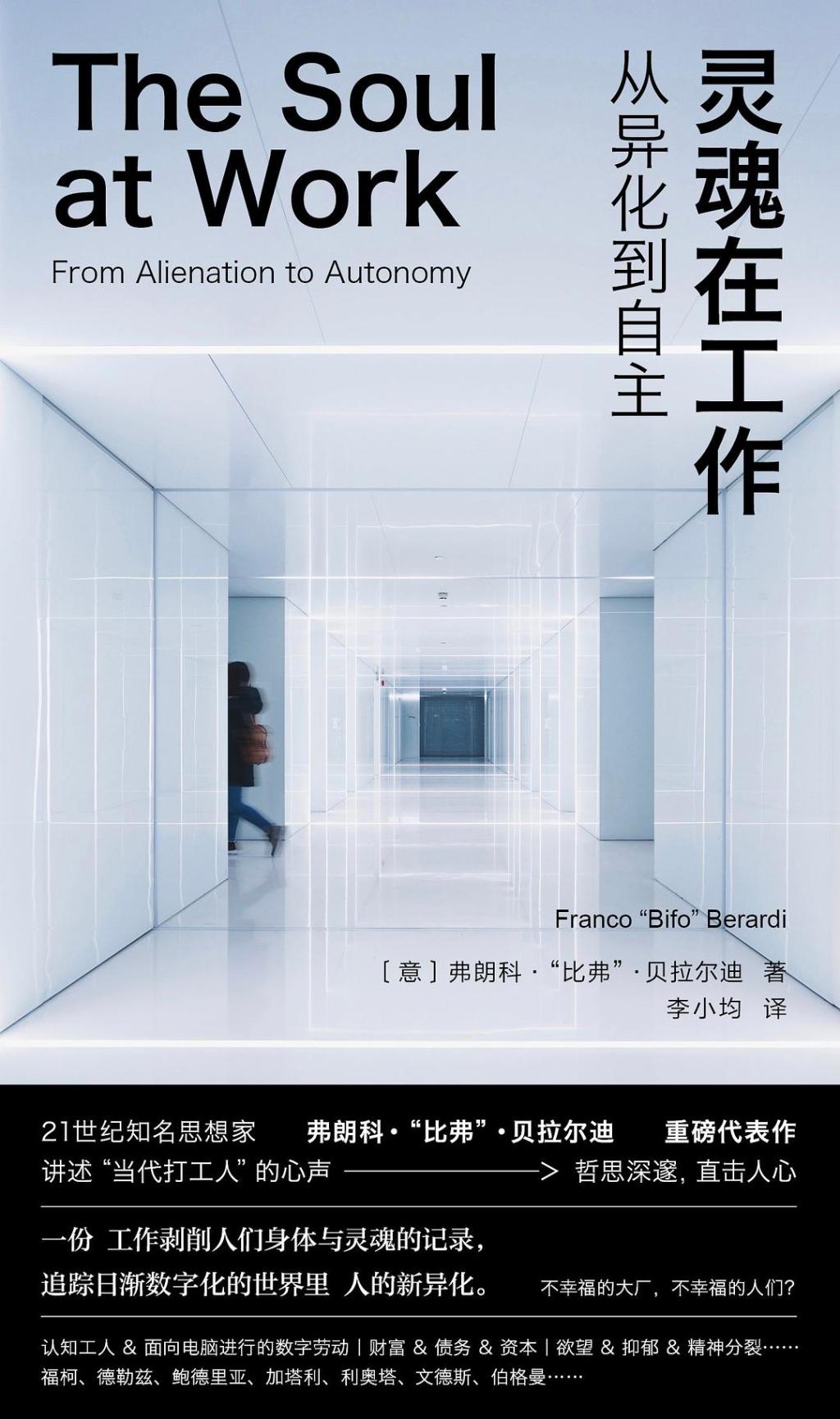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5
京ICP备2025104030号-2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